大运河历史文脉构成与理论范式研究
作者简介

作者:(图片为路璐)
路璐,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农业文明分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环境史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研究。
许颖,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全球化视野中,国家常以文化遗产来建构国家形象,争夺国际话语权。自上世纪末开始,西方“权威化遗产话语”就已形成对全球遗产言说方式的主导。在西方精英文化遗产话语的统领下,全世界遗产保护模式趋于一元化。我国在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并开始世界遗产申报后,文化遗产领域的观念和传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遗产话语的影响,遗产的物质载体被突出强调,本该贯穿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忽视。而事实上,与西方社会崇尚实证而获得客观对象“真实性”的认知习惯截然相反,中国人对于遗产价值的认知绝不限于物质形态,而在于它是否能够作为政治记忆的表达场所,传达出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精神再造的价值,这一点本应是在中国当代遗产话语中首先要提出的。
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文化遗产的当代语境,创新性地使用“历史文脉”这一概念,以此切入中国大运河研究,试图借此探索一种属于中国的本土遗产话语,这种话语的主体必须是民族国家,话语的宗旨必须是对国家认同的建构,话语的重心必须是遗产中的无形精神文化元素。从学术上说,这一点也是“历史文脉”与以往所有遗产概念最为不同的一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既有文化遗产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的一种补充和延伸,具有理论意义;从现实角度说,这又是对中央近年来持续推动延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文化遗产价值的国家战略的时代呼应,具有现实价值。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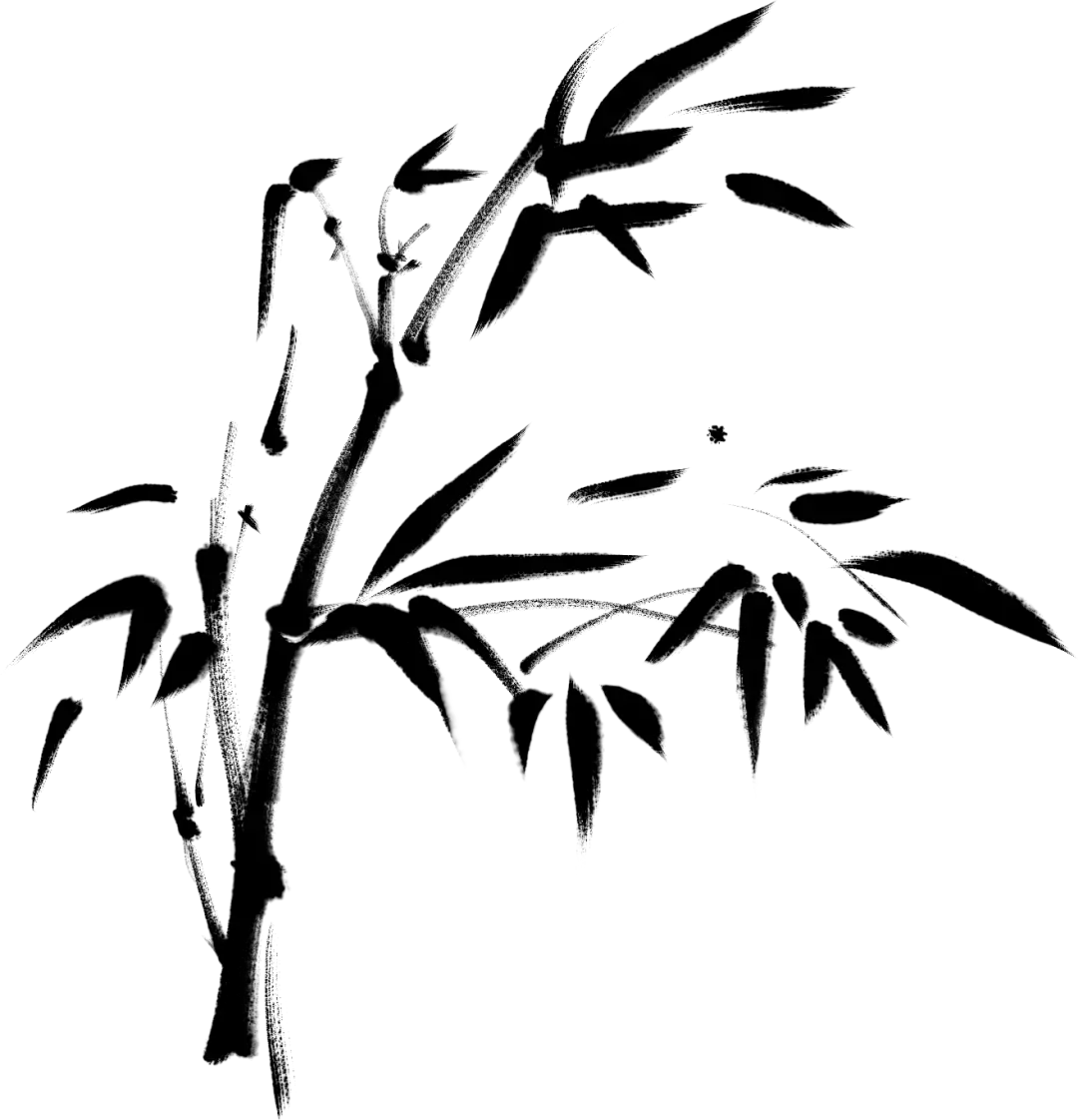
一、国内外“历史文脉”理论溯源
历史文脉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被模糊而广泛地使用,其理论指导意义和源头创新价值却被严重低估。鉴于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本文首先直面文化遗产中的“历史文脉”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力图统合中西方关于“历史文脉”使用差异的张力,同时结合词源、话语与价值等多个纬度,尝试建构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大运河历史文脉的理论框架。
(一)文脉、遗产与价值:国外历史文脉理论文献回顾
追溯国外文脉理论的缘起与发展,可以窥见文脉发仞于实体建筑、历史街区等物质遗产的保护之上,其理论发展脉络从空间向时间弥散。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罗伯特·文丘里极力主张文脉意味着建筑设计应与环境保持相互契合的互动关系。1966年,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提出文脉元素隐藏在文化类型中,而“类型在本质上同历史相联系”。1971年,美国学者舒玛什在其《文脉主义:都市的理想和解体》一文中正式提出“文脉主义”,认为建筑形态应该同文脉互为呼应,重在体现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1978年,柯林·罗在《拼贴城市》中提出文脉是不同时间范畴的产物,要“实现历史传统要素的重构与延续”,并从城市生活的主体——人的角度赋予文脉以新的内涵。上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黑川纪章以探求传统文化在现代的表现为切入点,倡导“共生哲学”,主张在多层次上继承传统。总之,文脉主义的理论建构聚焦局部与整体、实体景观与空间语境的关系。
历史文脉与文化遗产类型中的“文化线路”也有较深渊源,形与神皆有相似之处。在“形态”上,文化线路在地理区域的跨度上通常是超大尺度的,充分体现了“时间和空间在线路上的交互作用”,它所形成的文化景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连续性”。和文化线路一样,历史文脉也有主体多元的特点,它是不同群体在各自地理空间、历史空间内的文化创造,在时空的超长横纵线条上把文化遗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到了一起。在“神韵”上,两者的相似性表现在动态性与生成性纬度上。历史文脉承续了文化线路“动态性涵盖已经生成或仍在继续生成相关的文化要素”,以及“其无形的精神联结文化要素,促进文化线路整体形成”的精神内涵。历史文脉代表人们的迁徙流动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交往交互活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凝聚文化认同。历史文脉的动态性、生成性以及超时空尺度由此而生,强调的不仅是有形的文化景观,更是整体性视角下区域文化互动以及群体文化精神的变化脉络。
历史文脉还表征为对遗产价值的研究,因为“遗址的作用是由其被赋予的文脉表述所决定的”。如1979年《巴拉宪章》提出的新遗产价值,即“某一地点作为多数或者少数群体精神上、政治上、民族上的或其他文化上的情感聚焦时所体现出来的价值”,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提出“将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原真性置于固定的评价标准之中来评断是不可能的。相反,对所有文化的尊重,要求充分考虑文化遗产及其文脉关系。”
(二)道、史与文:中国传统语境下的“历史文脉”梳理
中国古代典籍中,“文脉”的“文”意指文章,“脉”则借“血理”之意,意指脉络。“脉”最早由南朝梁时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提出:“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意指文章从首至尾都需要内部的“脉”来贯穿。明代王文禄在其《文脉》一书中追溯了文脉的源头,提到“文肇始于上古,一直到明代,接一元之文脉,指人心之文原,美矣!至矣!”他认为古今文章的接续传承未曾断绝。
此外,“文脉”又与“国脉”“文统”“政统”关系密切。南宋吴潜在《魏鹤山文集后序》中提到:“潜窃谓渡江以来,文脉与国脉同其寿”。文脉可以视为文统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文统在各个时代的不同发展形态的表征,文统的承续就是文脉绵延的象征。值得一提的是,文统与道统密切相关,共同为文化政治服务,如阳明心学兴起之前,文统一直暗含儒家“文本于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脉有辅时治世的社会功能,“为文”需以“弘道”为目的。因此,“文统”以“文”为表达方式,服务于“政统”——一种“‘政治形态’或政体发展之统绪”,为政统的合法性张目。总之,文统以其服务于政统的文化政治性成为文脉得以内化于心的精神内核,由于文统的贯穿,文脉才可以承接过往、溯古推今。“脉”传承的是“道”,因而历史文脉不是不可断绝的,而是事在人为,必须依仗后世文化主体对文脉的延续与架构,文统才得以彰显与传承。
在中国传统史学语境中,“历史文脉”也可以从“史”“文”“道”三者的深层联系进行解读。文与史一体而两面,文与史使得难以捉摸的道有了具体的承载。“道非文不着,上天之载不可窥,而成象成形灿着于两间者,皆文也。”文的形式可以多样,“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但是无论如何演变,由于道的存续不断,文的源流也是一脉相承的,道不绝,文就不绝,文脉自然也就形成并延续下来了。与文类似,“史之义出于天”。史同样承载着道,但史又无法与文分割。《文史通义》载:“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事必藉文而传”,史承载的是“道义”,记载的是具体发生的事实,但却要通过文呈现出来,并以文的形式流传下来。所以文与史虽都是“道”的反映,但二者又不能完全两分或者偏废。偏于文,轻于史,则舍本逐末,史就不成为史,偏于史,轻于文,则史就无法达到微言大义、春秋笔法的效果,因此,“良史莫不工文”,“(良史)必通六义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文与史的统一,承袭了道统,又继承了文脉。在“道”的统摄下,“史”与“文”辩证生成,道、史、文共同构成历史文脉,也为中国本土遗产价值生成提供了深邃的历史渊源与丰厚的思想滋养。
(三)历史文脉的概念建构
综合上述理论源头,对于大运河这样的巨型线形文化遗产而言,历史文脉的概念必然含有以下三组重要内涵:
第一,历史文脉具有巨型时空体量,并构成纵横交织的意义网络。历史文脉在时间上拥有上千年的历史跨度,在空间上拥有超大面积的空间体量,因此它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纵横经纬结构上的网络——深层的文化结构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上分别延伸,多重时空的文化景观在历史文脉中连缀起来。历史文脉要求以更新的视角去看待广阔的文脉,去描述和保护与历史文化直接关联的遗产本体和环境背景,以及与整体价值相关的有形与无形遗产,因此“历史文脉”延伸了“文化线路”的动态性与深层文化结构,它更强调文化遗产所昭示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包含已经生成或仍在继续生成相关的文化要素”,而这些文化要素反过来又具有内在联结性和空间动力特征,“无形的精神内在连接多种文化要素”。历史文脉同时也是一个意义网络系统,即历史发展的纵线——按时代或历史朝代连贯形成纵的各个种类不可移动文物发展系列,以及历史发展的横线——把同一时代或历史时期中,反映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民族习俗、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文物联系起来,形成横的各个种类不可移动文物发展系列,进而交织构成纵横线上的史迹网络,反映一个地区的历史发展概貌。
第二,历史文脉包含实体与话语。话语是历史文脉的重要扇面,甚至可以说具有原动力地位。站在话语的维度,遗产其实是借文脉来彰显自己。“把遗址放到特定的文脉中呈现过去,就是一种话语行为”,所以遗产被广泛认为是一种话语实践。遗产话语也是个时间历程,“话语不仅可以作为解释和定义遗产的透镜,而且能够将过去引渡到现在”;遗产与当下产生共识的交叠,“是一种连接到过去并与我们的文化认同、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相关的文化过程或交流过程,遗产的词性已经从名词转变为动词”。
话语当然涉及主体问题,历史文脉必须是由特定人群共同创造、共同参与、共同享有、共同接受的社会产物和精神产物,“只有在被赋予价值之后,客观本体才进入所谓‘遗产’的概念范畴”,这是因为创造和共享文化遗产的群体正是基于自身需要将价值投射到文化遗产之上的,他们对遗产价值与意义的解读自然不尽相同,由此形成了“竞争性的文化认同”。历史文脉的另一主体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引领“政治性认同”这一遗产叙事方向的最高遗产表述单位,“个人被排除出他们自己的遗产”,这样做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政治权威合法化和正统性,以获得一种历史延续感”。
第三,历史文脉的命名昭示着文化政治进入历史场域。政治语法的深层结构发生在文化领域,且通常勾连历史经脉。我们可以看到,文化遗产中的“文脉”建设在一个变动的文化逻辑上,即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被质疑,代之以一个多重性、被赋予性、斗争性的价值空间。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自我显现中,封闭的历史本质主义向开放的历史文脉转化,而这一点恰恰与另一理论来源——文脉主义有着某种历史性的交叠。
“历史文脉”召唤着一套中国文化遗产的本土价值建构。这种建构本身就是一种思维范式,是对现行的西方权威化遗产话语的批判与反思,更是对其背后的西方线性历史观、西方普遍主义话语、文化遗产标准后的知识生产、白人精英的文化旨趣以及权力与意识形态操控等的批判与反思。可以说,历史文脉这一概念与表述的出现,本身就“呼吁一种完全属于不同文化思维的话语出现”,这种话语能够蕴含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与想象力。总之,征用“历史文脉”这个概念正是借助文化学、历史学、符号学等多学科理论支撑,构建出一套符合中国文化思维和遗产意义表述的新的遗产研究范式,最终建立起能够平视世界的中国遗产话语体系。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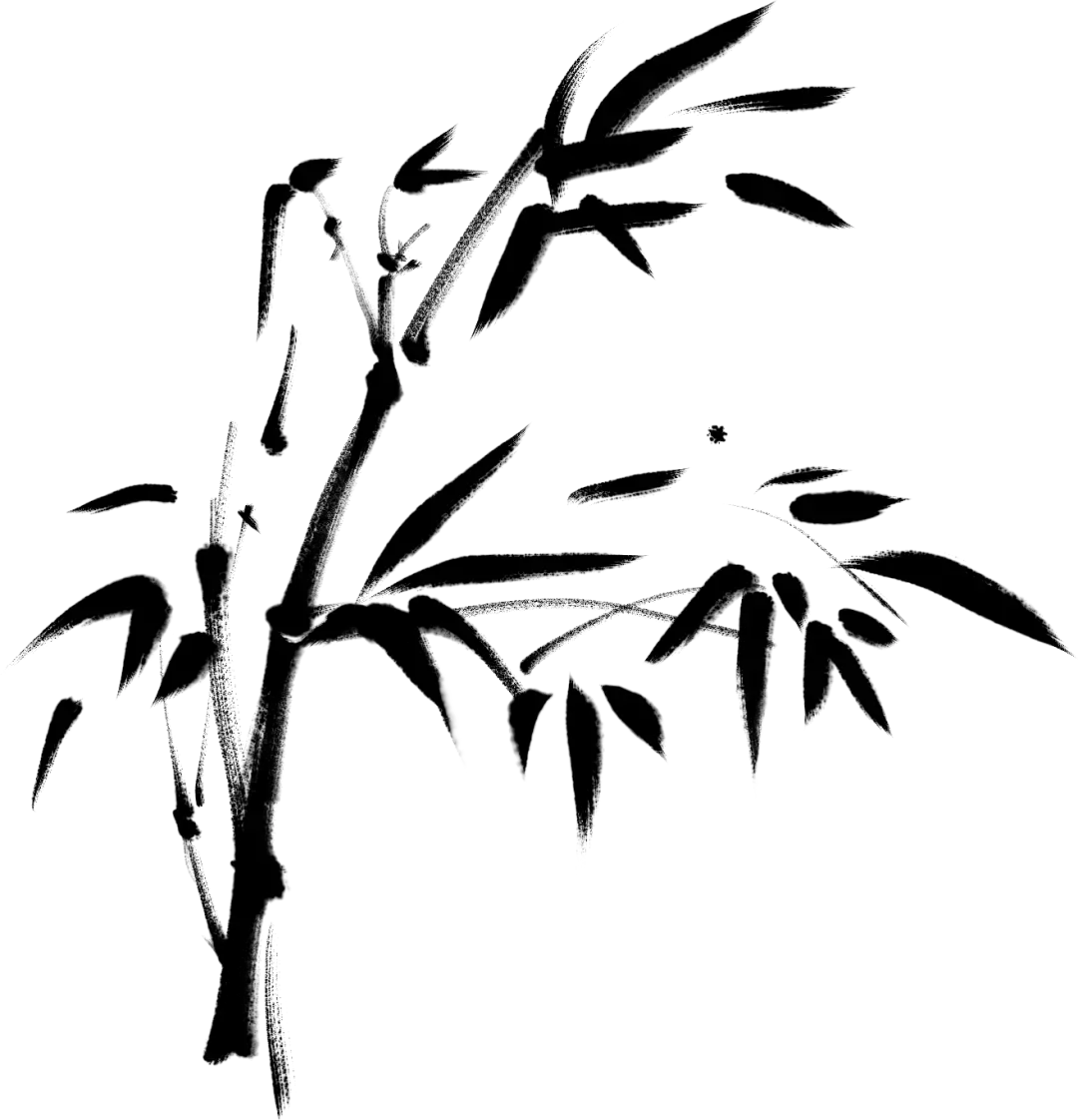
二、大运河历史文脉的概念与构成
历史文脉作为区别于现有文化遗产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及方法,以及一个新的文化遗产概念,融合了时空上所有的文化互动关系和文化遗产于一体,并附着在有形与无形的遗产之上,表征它的文明母体,正如《威尼斯宪章》对于文脉载体的描述——历史古迹与其见证的历史不可分离,历史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有形的建筑物,更包括藏于其中的一种独特文明。
大运河历史文脉是大运河在时间和空间上演化的历史文化脉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与中华大一统国家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大运河历史文脉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由漕运、水利、民俗、城镇聚落、文化遗产、考古遗迹、历史典籍等构成,具有多元性、开放性、流动性等特征,涉及国家与社会、整体与局部、传承与创新、实体与话语、记录与阐释等。特别是与大运河相关的历史事件、关涉主体、区域文化、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通过一条怎样的文化线路串联起来,它们如何被赋予时间上传承的价值与空间上流布的意义,它的文化基因与文化价值是如何支撑大运河从历史流向当下,并与未来建立起关联,都是当前亟需捋清和阐明的问题。大运河历史文脉具体由时空二重性、区域文化与华夏主体文化互动生成、显性要素与隐性要素的统一以及实体与话语四个部分构成。
(一)大运河历史文脉的时空二重性
《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实施指南》导言提出:“人民生活和活动于其中的结构应该有时间和空间两个向量。”大运河历史文脉聚焦大运河文化的起源、兴起、发展、繁盛、转折、复兴的演变历程,同样是具有纵向的时间关联性和横向的空间关联性的。
从时间维度上说,大运河最早开凿于距今2500余年前的春秋时期,经过秦汉三国时期的发展,区域性运河得到进一步完善,至隋唐时由区域性运河纳入全国性运河网,形成以洛阳为中心,南接余杭、北通涿郡的隋唐大运河。两宋时,以首都汴京和临安为中心的运河体系的建立,进一步优化了大运河河道网络。元明清三代,大运河截弯取直,不再绕道洛阳、开封,现代意义上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出现,并通过“去湖槽化”“去河槽化”的改造,实现河湖、河黄分离,运河周围历代遗留的众多河道也被利用起来,成为大运河的支线或者水源,大运河达到发展顶峰。经过清末民国的短暂衰败后,在新中国人民政府的修筑、扩建和现代化改造下,大运河实现复兴并逐渐向着数字化、信息化迈进。可以看出,大运河由中华民族共同修筑并延续至今,它的起源、发展、繁盛、转折、衰败、复兴等过程几乎贯穿了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
从空间维度上说,大运河的发展正是一个从区域到局部扩展的过程,其影响力和辐射范围在发展中不断增大。先秦时期各诸侯国通过人工运河将天然河道互相连通,形成了以邗沟和鸿沟为主导的沟通江、淮、河、济的区域运河网络体系。秦汉时,随着南方灵渠、关中漕渠的开凿,中原汴渠、鸿沟的完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珠江六大水系的区域运河网络进一步形成。隋唐之时,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大运河出现,南至苏杭、北至涿郡、中贯洛汴、西抵关中,从北至南、从东到西,全国性大运河实现了最大程度的贯通,大大加速了经济、文化在全国区域内的流通。两宋时,运河网络不断调整,大运河的辐射范围虽较隋唐缩小,但是随着堤堰为代表的运河修造技术的提高,大运河的效能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元明清三代,为进一步连接南方经济中心和北方政治中心,大运河经过截弯取直成为贯通南北、直通京杭的京杭大运河,将中国彼时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贯通起来。
(二)大运河区域文化与华夏主体文化互动生成
大运河文化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同时可视为大运河沿岸各个区域文化。但是,大运河文化并不等同于大运河沿岸各个区域文化的简单叠加,而应该视为立体构架。尤其重要的是,各个区域形成了一个共性,通过商品贸易、信息传递、文化交流形成了一种大运河的文化体制。另外,大运河文化体制一旦形成,它又深刻且持续地形塑了各个区域内的文化。隋唐以前,出于军事战争、交通运输等目的,区域性运河产生,运河文化在区域性运河沿线地区不断孕育。隋唐时期,大运河全线贯通,漕粮运输的需要使大运河成为连接南北之间的动脉,大运河对王朝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大运河的治理由王朝统一规划,大运河文化在王朝重视的政治环境中不断发展。明清时期,漕粮运输成为维护王朝安危的重要举措,大运河作为连接政治中心北京与经济重心江南地区之间的生命线,备受王朝的重视,自上到下形成了一种关注大运河的共识,大运河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趋于繁盛。大运河不仅仅发挥着南粮北运,解决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问题的作用,还承担着“中央政府的稳固、地方势力的限制、边境力量的加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消除”等重要功能,明人邱濬的评价“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天下矣”可谓一语中的。
大运河的开凿和运行有力地改变了沿线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体现了国家对各个区域的全局性战略部署,促使各个沿运区域在物质、制度、行为、精神、文化等多个方面和层次上发生了持续演变,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以联结与沟通为主要特质的大运河文化,从而强化了中华文化的整合性。从横向看,京杭大运河贯通中国最为重要的东部地区,其漕运航线及其它重要的人工运道盘桓在“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流经多个自然与社会条件迥异的大大小小的区域。这些区域共同成就了世界史上最长、航运规模最大的人工河道。历代运河在其发展过程中从空间上将中国由中原不断向四周扩展,将燕赵、齐鲁、淮扬、江浙、闽越、荆楚、关中等众多区域统筹于中华文化之中。陈春声指出:“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各具特色的表达,同样的,国家的历史也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出来。”大运河历史文脉的五色斑斓正在于区域文化与华夏主体文化的辩证生成。
(三)大运河历史文脉显性与隐性元素的统一
大运河历史文脉的构成元素分为显性元素和隐性元素两类,它们辩证生成。大运河历史文脉的显性要素主要是指与其有关的各种物质文化遗存,它包括运河本体遗存和相关文物,以及因河而兴的古城镇、古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建筑群等,暂可将这类显性元素划分为河道、湖泊、驳岸等河道类遗存,枢纽工程、闸、堤、坝、桥梁、水城门、圩堰、纤道、码头、险工等工程设施类遗存,衙署、驿站、行宫、钞关、仓窖、船厂等漕运类遗存,航运景观、水利工程景观、园地景观、林业景观、渔业景观等景观类遗存,古城、古镇、古村、古建筑群等聚落类遗存,商行、会馆、老字号等商业类遗存等。这些形形色色的物质遗存成为大运河历史文脉最直观的体现。
大运河历史文脉的隐性元素是不同群体在不同地域和自然条件下的文化成果,其中凝结了民族精神、族群心理认同和社会历史文化,这三者之间互相作用的同时也促成了历史文脉的动态演化。大运河历史文脉的隐性元素包罗万象,例如传统工艺、建造技艺、仓储技术、饮食习惯、民间文艺、传说故事、民俗节日、传统武术、宗教信仰等,暂可将其分为治国理念、治水思想以及与运河直接相关的信仰等大运河观念类遗产元素;大运河水利、河务、漕运等方面专门著作、专志、通志、地方志等文献类遗产元素;运河管理法规、漕运管理制度、民间规约等大运河法律制度类遗产元素;工程建设与维护技术、漕运管理技术、造船技术等大运河技术类遗产元素;与大运河有关的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等文学艺术类遗产元素;与大运河有关的宗教信仰、仪式、节庆活动及相关文化空间等大运河民俗类遗产元素;陶瓷、织造、漆器、印刷、锻造、建筑营造等大运河手工技艺类遗产元素。这些隐性元素既是大运河精神的象征符号,也代表着大运河文化不断变迁的“生命”本质,涵盖了它在具体时空层面生成、传承、革新的全部进程,标志着永不停滞的深层生命延展和丰裕久远的历史文脉传承。
(四)大运河历史文脉的实体与话语并存
从构成来讲,大运河历史文脉本身就包括有形的物质元素与无形的文化元素,因此大运河既是实体的,也是话语的。从实体的角度,不仅大运河河道本身是具有生命力的实体,而且以其为轴线串联起来的漕运、景观、聚落等诸多有形遗产元素也是大运河历史文脉具有实体性的有力证明。从话语的角度,我们强调的是大运河历史文脉的本土价值及其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西方权威化遗产话语的消极因素,大运河历史文脉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以文化群体的姿态去看待自身的全新视角,有形遗产可以由于时间的风化而消失,而历史文脉中那些如建筑风格、政治体制、传统技艺、习俗、宗教、艺术等无形文化元素,却因其能够传承不绝而赋予我们统一的文化身份,形成文化认同。以大运河河道治理为例,中国历史上秦、隋、元三次大统一都把大运河治理作为朝中第一要务,历代治河表面看是一项“治河即所以治漕”的水利工程,实质上也是一项延续政治惯性、维护祖宗之法、建构政权合法性”的国家政治工程,即对“道统”的延续与对“政统”的维护。
在历史中的大运河被当下话语召回时,运河空间本身也经历了空间重构,一方面这个空间是在实体空间的基础上,依托特定的河道、区域、无数支流在时间中沉淀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使民族国家可视化;另一方面也是列斐伏尔所说的“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承载民族国家记忆的建构。可以说,遗产是一系列话语、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叠加,参与一系列价值和理解的建构及原则的设定。但是,在当下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研究的前沿领域,亦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遗产规划和管理者应以中国特有的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为指导,进一步探索中国当代语境下的本土话语。”这就涉及到文化遗产更深一层的文化政治价值与主体性之争的问题。文化遗产既要有能力去拥抱历史上的骄傲,也要有能力去总结,去跨越历史的缝隙,去面对整体历史生活的复杂性、矛盾、悲剧与选择。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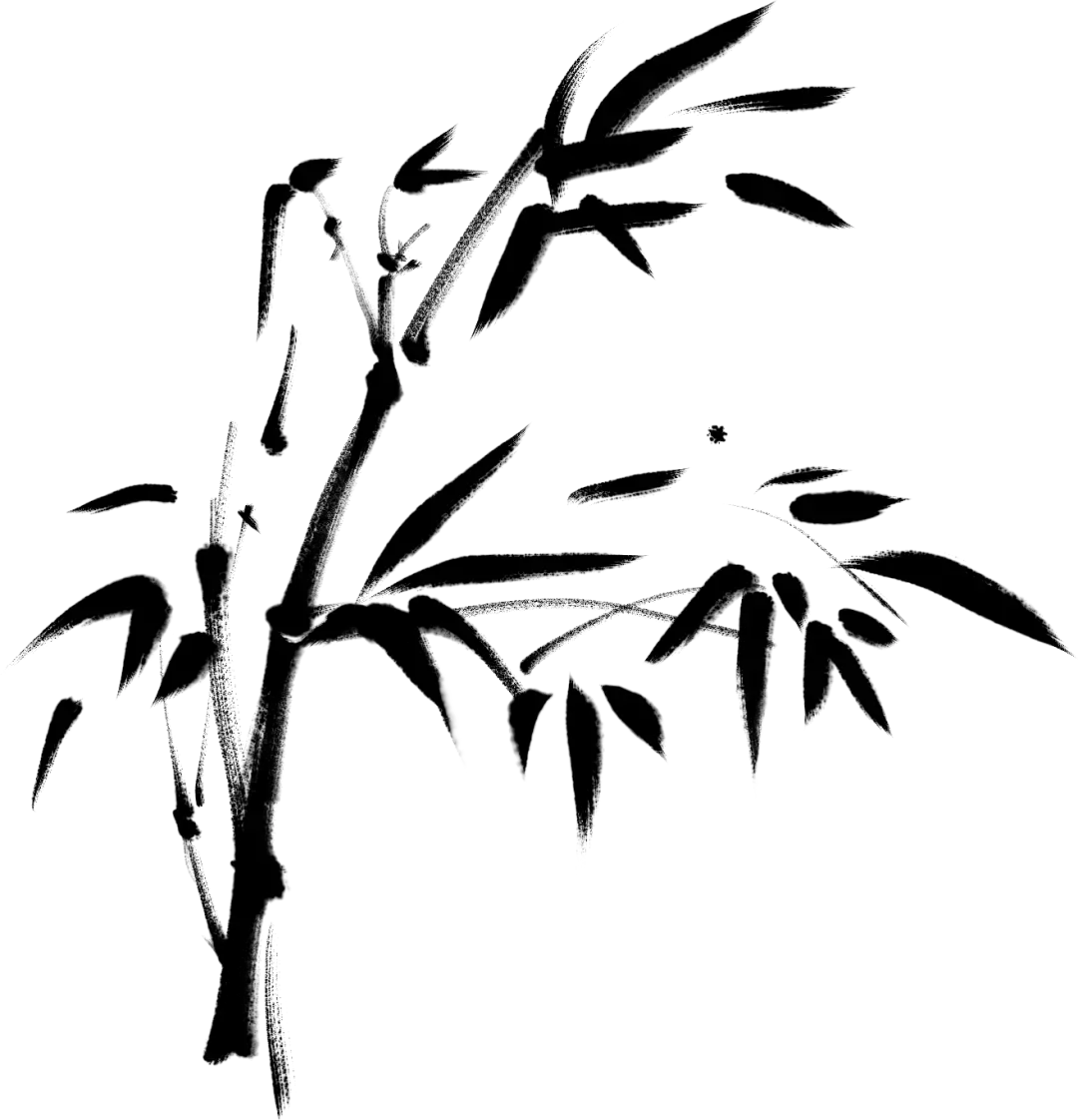
三、大运河历史文脉的理论范式:
回到历史场域的文化政治
中国大运河虽现已成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序列,但过程却非平顺。各国运河遗产关于遗产申请、遗产价值认定以及遗产保护均受到西方权威化遗产话语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下的遗产实践格外强调世界遗产应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f heritage,OUV)”,尤其注重“技术、经济、社会与景观”四者在价值认定中的地位。在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主持编制的《国际运河古迹名录》中,尽管法国米迪运河的规模仅相当于中国大运河的“江南运河”段,在建造时间上更是相差甚远,但前者依据其技术、结构与建筑特征等在所有运河遗址中被评为最高等级。而中国大运河在申遗时却不得不扁平化大运河所具有的多样性价值,“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大运河的评估中纳入了文化标准(i),(iii)和(iv),以凸显大运河的合理性,且重点关注其纪念碑、建筑和技术价值;然而在标准(vi)中,无论是事件或生活传统、思想或信仰、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艺术和文学作品都被其否定”。对此,有学者就犀利地指出,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性部分被西方权威化遗产话语选择性地遗忘了。大运河遗产价值中那种生机勃勃、无形却不朽的东西不能为世界文化遗产现行标准接纳,这当然令人遗憾,但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来说绝非个案、绝非偶然,如西湖在申报时也是如此。西湖申遗起步很早,但其申遗过程却耗费十余年,究其原因,就在于西湖虽然汇集了中国古代儒释道文化的各类遗迹,承载着丰厚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但在代表西方权威化遗产话语的UNESCO和ICOMOS等国际机构的专家面前,这些却并不能成为西湖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证明,最终西湖以其代表的“诗情画意”传统文化及其对东亚各国景观设计的影响得到认可,而完整的西湖文化价值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是缺位的。这其中的遭遇发人深省,也吁求文化遗产领域中一种新概念与新范式的出现。
大运河历史文脉作为一种概念生成与理论范式,首先体现在历史领域。表面上看遭遇的是权威化遗产话语,实际上遭遇的是西方普遍性话语的强势与追求唯一性的统御力。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东方定位在“非历史的历史阶段”,并在鸦片战争的前十五年,他就提出英国征服中国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历史被引入政治场域,成为民族生存的基础,民族国家也被迫以历史作为自卫的武器,而文化遗产这种话语的主体正是民族国家。大运河历史文脉的建构不能驱除历史性。“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性的经验是以各种不同的叙事或非叙事的方式来记录的,如文学、神话、谱系、艺术、仪式、语言等等。”历史文脉的历史延展性可以借用杜赞奇“符号的复刻”来说明问题。简言之,文化符号可以做到既连续又断裂,这被称为符号的复刻。所有的历史故事、文化象征、民间传说等如果没有做到复刻,将很容易散佚在历史变迁的浪潮中。所以“文化符号即使在自身发生变化时,也会在某一层面赋予社会群体和利益的变化以一定的连续性”,也就是说,文化符号既连续又断裂的原因正是历史、社会共同体既连续又断裂。大运河作为巨大的文化象征符号,复制的话语力量来自于文化积淀,它通过历史层层累积的效应指涉个体认同与意义共享,在不同文化群体中建立一个实现各种社会诉求的文化身份认同,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社会共同纲领”。值得警惕的是,我们在实践领域中常常忽略了这种“复刻”,在大运河文化国家公园、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大规模的再生产与再意指势在必行,但“复刻”却必不可少。
其次,在文化政治领域中,大运河历史文脉需要在空间上整理混乱与克服他者性的历史实践,在时间上承接中国传统史学思想脉络中的文脉即国脉,文统承载道统,道、史、文三位一体的文明沉淀,在某些自身的断裂与矛盾处重新建构为创造性与整体性的反思与表述能力,不断生产出意义空间与解释框架,带来一种文化与政治的辩证统一。
大运河历史文脉建构不仅仅是一个回归传统的问题,它还是与当下对话后的再建构,它至少由同心圆的三部分构成:第一同心圆是历史上存在的大运河,即作为一种过去事实的历史元素从古代到近现代一直流淌着的大运河,包括河道本身及相关遗址,它是作为事实的存在与遗留物的存在。第二同心圆是历史中的大运河,包括典籍、大运河记忆等。第三同心圆是在第一与第二同心圆的基础上,当下主体对其进行系统性梳理、补白、连缀与建构,形成的一条清晰的、能逻辑自洽的历史文脉,包括大运河如何发挥独特历史作用,大运河如何以“舞台”承载历史的变迁,同时也聚焦分析历史重要节点如何改变了大运河的政治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以及当时空间中生存的主体。所有的大运河历史事件进入历史文脉后,被转译成一个个符号、一个个象征、一个个特定的意义。历史文脉也是主体赋予了符合当下实际的文化政治,是超越时间的时间之地,是穿越断裂与遗忘的重构空间,是从历史中挖掘走向当下主体的文化记忆。在全球化时代,对大运河历史文脉的征用需要沿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徐徐展开,其历史叙事除了逻辑自洽,还需要自我理解与认同。
大运河历史文脉的建构还需要拥抱现代性。简而言之,对于中国而言,打造大运河历史文脉就是把特殊的历史经验理论化,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改写现有规范。从当下的语境看,面对全球化语境中文明的断层线以及西方话语在现代性话语中一贯的强势地位,中国急需征用合适的巨型文化符号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说好自己的故事,征召更多的主体认同自己。大运河历史文脉应把回归传统与新的生活世界连接,最终建构一个新的价值平台,肯定自己并向一切非西方价值体系开放。当然,也需要与西方现代性话语积极对话。
此外,必须明确的是,大运河历史文脉这一理论范式是一个全新的总体性范式,并不是西方普遍性话语遗产规则之下的特殊性遗产形式。正如杜赞奇在罗伯特·杨与伊曼纽尔·莱文那斯的研究基础上发现的关于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与总体性文化框架生成的奥秘:历史不仅为西方征服世界提供了合法依据,同时也把“他者”当作一种知识,于是,普遍化的历史一旦成为一种“话语”与“标准”,就可以肆意把其他任何非西方的社会和知识形式纳入自己,纳入只以自身为依据、凌驾于一切的框架之中,它或可以让后者完全迷失,或可以让其处处捉襟见肘,甚至可以作废其他的文化心智。这是西方哲学中有关总体性观念的一种运行方式,其残酷之处就在于西方一面把自身的特殊性伪装成一种普遍性话语去征服“他者”文化,另一面它隐秘地靠摄取和扬弃“他者”来生产知识。
大运河历史文脉以中国意识直面近代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它并非作为一种特殊性存在,它要挑战的是西方遗产话语的总体性框架。换而言之,它不是“一”之下的多,而是另一个“一”,即另一种普遍性与总体性,而普遍性表达的最终状态往往不是多样化的个案与审美意义上的文化遗产,而是遗产领域的“法度”与规则。因此,当下亟需出现一个能代表文化遗产总体性的概念与全新的理论范式,征召“历史文脉”这个概念的意义正在于此。大运河历史文脉作为批判的范式,它要放逐西方权威化遗产话语中的“原真性”。究其本质,历史文脉与西方权威化遗产话语对于“原真性”的理解南辕北辙,“原真性”在西方线性史观的思想背景中,除了追求物质性,更是“将历史偶然变成一个长久的命题与关注点”,以此成为文化遗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价值准则,并作为西方普遍性话语与霸权价值在遗产领域的凝聚。莱文那斯认为“他者”抵抗扬弃的惟一方式是从历史之外的时间中推演出意义。大运河历史文脉以巨大的时空体量,显性要素与隐性要素的统一形成一套自洽完整的系统,因为中国文化在西方普遍性话语面前的自我辩护、自我肯定必须是完整的,只有保持完整才有可能形成有意义、成体系、成建制的价值系统、文化系统。而“历史文脉”这一命名深嵌在中国史学与文化传统之中,在“道统”的统摄下,结合文与史,放逐偶然性并在历史经纬的梳理中追求历史必然,追求“天命”。
大运河历史文脉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大运河作为巨型文化媒介,可以实现历史、现实与当下的对话。从历史上看,大运河与“国命”相交织,在古代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中也有重要作用。大运河蕴藏着巨型文化遗产“点、线、面”以及“水、岸、城”,这些沿线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能放到特定的文脉中呈现,并进行言之有物、逻辑自洽的景观建构与历史叙事,是当下理论建构的关键问题。大运河历史文脉是一种主体对大运河历史遗产意义系统的再整合以及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承续,“对遗址的记载就是裁剪不同历史时期的碎片,指引我们看见并理解生活世界的一个空间”。可以说,正是当下主体对历史片段与文化基因的双重编织形成了大运河历史文脉,而对遗产中历史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的传承是其贯穿始终的精神内核。







